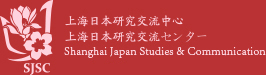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10月21日,日本临时国会将进行首相指名选举。公明党退出与自民党的联盟以及民粹主义政党渐成气候,令日本政坛格局碎片化。未来日本内外政策将发生什么变化?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白如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笪志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政治陷入“碎片化困境”
项昊宇
近来,日本政坛陷入持续动荡,首相一度“难产”的背后,是日本面临的深刻发展困境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尽管目前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仍有机会当选新任首相,但等待她的绝非坦途,而是空前严峻的内外挑战。
2023年底爆出的自民党议员收受政治献金回扣的“黑金丑闻”持续发酵,使自民党接连丢失众参两院多数议席,也导致其与公明党长达26年的携手走向破裂,重创了其执政根基。面对老气横秋、积重难返的传统政党,日本民众表现出厌倦情绪,把选票投向了新兴政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具有民粹色彩的小党崛起,使日本政坛格局碎片化,内外政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日本政治动荡的直接后果,是加剧政策的短期功利性,尤其是在民粹政治抬头的当下。朝野政党激烈的政策路线之争背后,是权力和利益之争。在自民党和维新会围绕组建执政联盟的政策磋商中,焦点议题在于削减国会议员人数和大阪“副首都”构想,而非外界关注的政治献金制度改革和经济民生议题。削减国会议员人数会触动既有大党利益,又能削减财政支出,迎合了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不满情绪和改革诉求。而对政治根基在大阪地区的日本维新会而言,一心想要让大阪获得部分首都功能的转移,多少会让外界觉得私心过重。因此,这些改革并不直接事关日本整体经济民生的改善,遑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日本政局不时出现动荡,首相频繁更迭,似乎并未影响到日本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日本经济的表面繁荣和社会的高度稳定背后,是发展的长期停滞、创新活力的衰减,国力走在一条漫长的下坡路上。以美元换算的日本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水平30年原地踏步,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巅峰时的18%已经萎缩至不足4%,所谓“失去的30年”并非虚言。
根本上而言,日本突破发展困境需要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日本经济长期依赖出口产业和国内消费市场驱动的既有增长模式,对内面临人口萎缩和劳动力短缺等深刻危机,对外面临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高市早苗主导推进的“经济安保战略”,试图通过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维护本土产业优势和技术壁垒,来维系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但此举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内需见顶和创新动力不足的困境。相反,在日本最需要吸引外劳和海外游客的时候,自民党却与维新会在强化外国人管控方面达成一致,迎合了右翼势力的排外主义风潮。
此外,日本积重难返的少子老龄化和债务风险要求跨越代际的长线解决方案,但选举政治的重压使得政党政客无暇顾及深层次改革,也缺乏政治魄力和持续投入去执行长期战略。至少在今后几年,疲于自保的短命内阁更缺乏足够的政治资本和时间窗口去推动这些变革。
在外交和安保层面,面对大国地位旁落的危机,右翼保守阵营主张打造“强大日本”的政治愿景,但无论是推动增加防卫开支,还是修改和平宪法,都蕴含着潜在风险。激进的强军扩武面临国内财政制约,也势必引发地区国家警惕戒备,加剧日本的安全焦虑。同时随着和平宪法被逐步架空,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软实力资产和道义招牌也会进一步被折损。而日本右翼保守政客在民族主义上的诉求和修正主义历史观,可能助长新政权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上的冒险主义,引发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冲突,进而恶化日本的外部环境。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在其实际政策的反作用力下只会取得事与愿违的结果。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是特殊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未能解决治理问题的结果。从经济停滞到人口危机,再到僵化的战略思维和行政体系,解决这些结构性难题,决定了日本更需要一个拥有强大民意基础、长期执政能力和清晰改革蓝图的稳定政府。
无论谁当选首相,执政路都不会平坦
白如纯
随着10月21日首相指名选举临近,围绕能否再度实现历史性“政权更迭”,日本政局一时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乱象。目前,由于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协商将于20日签署成立联合政权的协议书,高市早苗当选首相的可能性正在增大。不过,围绕此次首相选举所暴露出的日本政治混乱短期内不会结束,总体右倾化氛围下,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值得密切关注。
不久前,公明党宣布退出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犹如在日本政界抛下了一枚震撼弹。公明党的退出标志着自公执政联盟内斗表面化,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局混乱。自公两党联合执政近四分之一世纪,但公明党和自民党终究是两个拥有不同理念的政党,两者关系破裂并非“一日之寒”。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自民党的警醒。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为迎合部分保守群体,置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期待于不顾,重用有“黑金”政治“污点”的萩生田光一等,最终导致公明党与之“划清界限”。
随着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各党围绕首相提名选举的博弈白热化,带来政局走势的不确定性。高市早苗能否如愿当选新首相一度成为未知数。按照选举规则,如果第一轮没有人过半数,那么得票多的前两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得票简单多数者当选。因此,自民党能否拉拢某个在野党加入联合政权以阻止在野党实现联合,成为日本政治乱局的关键看点。
为实现政权更替,立宪民主党多次主动示好国民民主党,推选该党代表玉木雄一郎为新联合政权首相。但倚仗精于政治算计的麻生太郎等自民党大佬的加持,高市也在分化在野势力,拉日本维新会(在议会中占据35席)联合执政便成为合理选项。但无论谁当选首相,其执政之路都不会平坦。即便高市在维新会配合之下勉强当选,其政权运营与石破茂内阁相比恐将更加困难。法案或预算等棘手问题的解决需寻求在野党合作,会出现内外政策被掣肘的尴尬局面。反之,如果在野党间讨价还价,使联合执政成为现实,缺乏共同执政理念的各方势力也很难长期共处。日本政坛或将再度陷入“一年一相”怪圈,影响其内外政策的连续性。
日本政治光谱已经整体右移,不过其与近年欧美国家的“右倾化”似有不同,欧美式右倾化浪潮具有明显的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特征,而日本型右倾化的特点则表现为保守、传统的国内政治倾向。因为日本并非传统移民国家,其相对排外的右倾化更多表现为历史修正主义和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等内向型特征,如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宪法和扩大集体自卫权等。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作为极右翼政党代表的参政党获得14席,席位数大幅上升引起舆论哗然。以参政党异军突起为标志,日本政治右倾化呈现新形态,以往不被看好的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成为新兴政党的重要主张,也成为选举中辩论的焦点。打着“日本人优先”等口号,围绕“外国人问题”为中心阐述政治主张,以此获得选票。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等自民党政客也大肆鼓噪“外国人问题”以博取眼球。
总之,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耦合若成功,其组建的联合政权将面临挑战。一旦日本政党政治陷入混乱,民粹主义将顺势抬头。自民党已因“政治与金钱”等劣迹造成信任危机,如果朝野各方势力以宣扬民粹主义争取上位,或操弄“排外”议题谋求政治利益,对日本政局未来走向的担忧就不是小题大做了。
“双右”联手,东北亚合作受冲击
笪志刚
由于日本维新会选择与自民党展开联合执政磋商,放大了催生极右政权的可能性,“双右”政党联手将加速日本政坛向右转。由此带来的冲击波可能不仅将反噬其内政,因新政权保守的外交、安保、修宪政策,针对二战史观认知、在日外国人的偏激应对等姿态,或将带给周边国家更多不确定性,尤其带给东北亚区域合作更多担忧。
首先,日韩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李在明执政以来延续了改善对日关系的基调,两国“穿梭外交”也已展开,但横亘在两国间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并未彻底解决。若日本政权未来更加右倾保守,争议与矛盾也将随之而来。
其一,历史认知再次成为焦点。作为激进的右倾政客,高市早苗不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还将日本在“慰安妇”、“战时绑架劳工”等历史议题上的对韩道歉视为 “自虐史观”,宣称在历史认知上决不让步,其强硬姿态或将导致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再度对立。其二,领土争执重新发酵。高市主张对竹岛(韩国称独岛)拥有主权,公开称官员应出席“竹岛日”活动,并称“没有必要看对方眼色”,这可能令日韩改善关系遭遇急刹车。其三,美日韩合作或将受到影响。美国一直努力撮合日韩改善关系并服务于自身的“印太战略”,岸田等内阁也做了一些推动,但未来日本内阁可能更依赖保守选民支持,韩国在选边站和对朝强硬上的压力加大,将影响两国深化安保互信,甚至冲击美日韩合作本身。
其次,中日关系或将面临新挑战。高市此前在事关中日关系方面的观点、立场和主张一直备受质疑,其言论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稳定及两国民意互动的负面因子。未来若日本政界走向保守政治,将对中日关系造成冲击。
一是历史问题和修宪企图引发民意对立。日本右翼保守政客围绕二战历史认知的所作所为一直遭中日民意抵制,而且该阵营的底色基本为修改日本宪法的推动者,对组建“国防军”持积极推动态度。这些都将触碰中国民意的底线,引发民众对日本右倾化及混乱政局的警惕。
二是政治因素或将影响经济互动。公明党脱离执政联盟可能会让自民党未来在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上进一步转向防范和遏制,经济安全和所谓“去风险”将成为遏制筹码。经济防范和安保遏制双重因素或将导致经济交流遇冷,中日应避免重陷“政冷经冷”。
最后,东北亚区域合作可能将受到日本混乱政局波及。明治维新以来近160年的日本近现代史证明,日本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扮演了区域动荡麻烦者和稳定机制破坏者的角色,如今日趋右倾化的混乱政局,让人再次担忧其是否重蹈历史覆辙。
一方面,未来日本内阁将强调日美同盟下的外交服务国家利益,支持突破“专守防卫”,构筑“反击能力”,其加强军备的理念将破坏域内的均势平衡,加剧相关区域的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的政治互信基础恐将遭遇冲击。日本右翼保守阵营鼓吹“经济安全”,也曾主导泛安全化的立法。其强化经济安全将产生投资审查、技术管制、供应链脱钩等恶果,不仅损害东北亚正常经贸往来,使东北亚区域合作趋于降温,也将影响区域合作的制度和互信基础。
旅游等人文及民间交流一直是东北亚合作的不竭动力,也是保持东北亚良好氛围的基础。希望未来日本内阁避免渲染歧视外国人言论,不要尝试推动防范外国人的立法,因为这不仅将激活本国民族主义情绪,还将直接影响人文交流,拉低民众相互理解和往来频度。越是在关键时刻,中日韩越应该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的民意及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