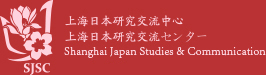编者按: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于10月17日举办了主题为“一年一相后的中日关系走势”青年学术沙龙,现将与会者精彩发言摘编以嗜读者。

褚冠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一、一年一相问题
最近20年来,日本政坛已经是第三次呈现一年一相的现象。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三次内阁频繁更迭期实际上都是对上一个长期内阁期间激进改革的反弹和回摆,也反映了日本政党政治内部再平衡的多向度过程。
自2006年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阁开始,日本政坛出现第一轮“一年一相”的频繁更迭,实则是对于小泉纯一郎内阁期间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加强首相官邸集权的反弹。自民党内遭受重创的派阀政治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卷土重来,实际上大幅消解了小泉内阁取得的很多政治成果,也加剧了自民党政治的民众失信感。而2009年政权更迭后,民主党整个任期可被视为第二轮“一年一相”。民主党为了兑现选举公约、凸显自身革新色彩,推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进而引发内政外交上的种种挫折。从鸠山由纪夫内阁时期追求政治主导到菅直人时期向官僚妥协,不仅是民主党政权初期大规模改革脱离实际的体现,也进而激化了固有的内部派系间路线分歧,最后也使得民主党在下野后走向分裂。
而从第二次安倍内阁结束之后,菅义伟和石破茂内阁也都只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岸田文雄内阁稍长。而随着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下一届自民党内阁的存续时间也面临挑战。宏观上看,日本政坛已经进入第三个“一年一相”的频繁更迭期。而这个时期的各种政策确实呈现了对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政策负面效应的修正和调适。特别是黑金丑闻所带来的派阀解散潮,更加使得自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重组呈现了新速度和新维度。派阀政治或许不会从日本政坛彻底消失,但是其结构和动力学较第一轮时期已有相当显著的改变。
二、意识形态结构
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是新生代日本保守政治家的典型。但是关于保守化和右倾化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众说纷纭。在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的过程中,保守主义在日本是增强了还是衰弱了?这本身就引出了对战后保守主义的结构认知问题。战后保守主义不同于与天皇制和国家主义纠缠不清的战前保守主义,实际上更多地是继承了战前自由主义的脉络,并通过与战后新一代民族主义以及官僚威权主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全方位型意识形态。如果要提取其特征,那么可以概括为发展导向、注重稳定、民族意识和有限理性的保守主义。战后保守政党在这些共识基础上,实现了对囊括左右的广谱政策适应能力,充分发挥了自己灵活调整、稳定发展的特点而实现了长时间的一党独大。
然而随着90年代以来党内自由派的衰落,战后保守主义的结构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失衡现象。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党内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增强,自民党开始失去了对社会民生议题的有效回应能力,不得不依靠与中道政党公明党的执政联盟来弥补缺陷。于是自公执政联盟就呈现了自民党维持金权政治大框架、党内保守派通过右倾政治表演满足保守选民需求、公明党回应对政治议题不敏感的中道选民诉求这样的双重嵌套结构。换言之,公明党取代了自民党内的自由派,成为了融合社会民生政策的“外包商”。双重嵌套结构固然使得自公政权能够在自民党不断右倾的同时还能维持广泛的选举支持,但是也挤压了自民党内自由派的生存空间。石破茂在刚刚担任首相的时候被誉为“新自由派”,并被寄予厚望对抗党内外兴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但是石破茂这种复古的新自由派也无力改变党内势单力孤的困局。而这种“外包模式”本身又扩大了对公明党的依赖。这使得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成为了自民党难以承受之重。新保守主义的基础源于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但是从学说出发建立的宏观政策体系势必无法包括社会诸象,也势必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革之际失去适应力。外包模式本身只是权宜之计,反映的恰恰是战后保守主义的局狭化和中空化。新保守主义不再以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为前提,而这恰恰背离了保守主义自身的根本逻辑。保守主义的衰弱反映的是其自身的结构性变迁,而催生的则可能是更加依赖抽象学说和主观情绪的极右意识形态。
三、中日关系
在保守政党主政但又自身挑战重重的时代,对中日关系的眺望离不开对日本政治周期的观察和理解。战术上,我们需要做逆周期调整,既要重视当下一年一相的调整期,也要为调整期过后下一个有志推行激进改革的强势内阁时期提前做好准备。战略上,我们需要做超周期布局,要抓准日本政治意识形态中核心要素,以逸待劳、以点带面地准确定位中日两国的合作面和摩擦点,在动荡的局势中维护我国主权和核心利益,并且共同造福东北亚的和谐稳定。